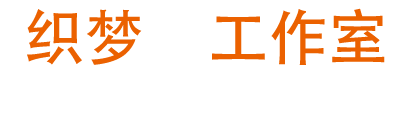独家专访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斯洛:他在
- 编辑:皇冠APP官方下载 -独家专访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斯洛:他在
 1985年,31岁的克劳斯·瑙霍科伊·拉斯洛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撒旦探戈》,成为匈牙利文坛最受欢迎的作品。从此,他开始了他的创作之旅。 2017年,《撒旦探戈》版本出版。 《北京新闻周刊》曾对Klaus Nahuholkay Laszlo进行了长篇专访。以下为全文。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将授予匈牙利作家克劳斯·瑙霍尔凯·拉斯洛。匈牙利小说《KrasnoHornaj Laszlo》将卡夫卡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当我不读卡夫卡的时候,我就会想她。当我不读卡夫卡的时候,我就会想她。她走了一会儿后,我就拿着她的作品继续读。”他认为自己和卡夫卡的K有一些相似之处。和卡夫卡一样,他大学也学的是法律,纳格或许准备继承父亲的事业,但烦人的法律职业并不能满足他浪漫的灵魂。 1985年,31岁的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撒旦唐》于是,他一心一意,便成为了匈牙利文坛最著名的人物。此后,他开始专心写作,完成了七部长篇小说、链式结构令人惊叹的小说。克拉斯诺霍纳吉·拉斯洛,1954年出生,匈牙利作家。2015年布克国际奖获得者,代表作有《撒旦探戈》《反叛的忧郁》。 其风格特点是句子长而复杂,结构现代。然而,读者却很难走进他的小说。首先,语言是一个外部障碍。作为一门小语种的古老语言,匈牙利文学不仅与中国读者感觉相距甚远,而且与欧美读者的感觉也由来已久。最初享誉全球的《撒旦探戈》出自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改编。这部七小时的电影 被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知识分子成功捕捉到,这使得匈牙利文学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2013年,匈牙利诗人乔治·希奇将匈牙利语原著小说翻译成英文,让英美读者真正感受到了《撒旦探戈》的美妙。此后,克拉斯诺霍纳伊的作品一直被单独翻译,译者都是匈牙利诗人——他总能找到唯一合适的译者。 2015年,克拉斯诺霍纳伊荣获曼布克国际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匈牙利作家。今年,通过翻译余泽民,他终于有了该小说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但即使从匈牙利语转向中文,他的小说仍然在考验读者的耐心。除了长句形式之外,克拉斯诺霍尔凯的世界充满了人类的集体挫败、生命的无意义和悲伤的生物。任何人在阅读的过程中都会感觉自己成为了卡夫卡笔下的K,在指定的世界之外继续漫游,无法进入。卡夫卡曾经表演过他的短篇小说里描写了无数山洞里的人,用内心的突变来描述令他内心悲伤的噩梦般的场景;而克拉斯诺霍凯是一个卡皮谈话人物,他写马龙小说、外面的场景,以及人类集体的悲伤和沮丧。他把人们带到那座城堡,关上门,向他们展示了生活的徒劳,以及安徒生红鞋般的探戈舞步。采访与写作|新京报记者 龚照华 对话翻译| 《撒旦探戈》译者于泽民·克拉斯诺·霍纳吉·拉斯洛是一个需要深呼吸才能读得有气无力的名字——如他小说中的长句,获得无穷的分量。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他是一位非常熟悉的作家,《撒旦探戈》也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但事实上,他早已在文坛闯荡,也多次来过中国。他对李白和儒家经典的理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更深的卡亚。他还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好丘”,意思是美丽的山丘,以及他对孔子的热爱。克拉斯诺霍卡伊·拉斯洛(Krasnohorkaj Laszlo)1954年1月5日出生于匈牙利久洛小镇。他的小说经常以匈牙利小镇的酒馆为场景。但单一国家并不能满足他的愿景。在完成他的处女作《撒旦探戈》两年后,他带着奖金离开了匈牙利,开始了他作为世界公民的旅程。首先是西德、法国、西班牙,然后是美国、意大利、希腊,最后是日本和中国。他在中国向游客讲述李白,并在纽约追随梅尔维尔的脚步。克拉斯诺霍凯目前住在德国柏林的家中。 《设定撒旦探戈》:【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卡伊·拉兹洛 译者:于泽民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7年7月《撒旦探戈》之前的写作和烧录 新京报:斯洛伐克有一座和你同姓的城堡。你认为你和它有联系吗? (城堡毁于一场大火几年前)克拉斯诺霍卡:一座匈牙利城堡位于斯洛伐克的克拉斯诺霍卡。这是一座有近八百年历史的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它被划分为匈牙利领土的一部分并被割让给斯洛伐克时,这座建筑成为了一个象征,有人写了一首关于它的歌曲,在匈牙利全国闻名,但那是一首可怕的歌曲,每次听到它,我都会脊背发凉。然而,在我们家,我的祖父很喜欢这首歌,并在一家小酒馆里整天唱这首歌,并决定用这个地方作为他家族的名字。这是我们以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名字,而现在,所有具有政治敏感度的出租车司机——一旦他们在向我开具发票时发现了我的名字——就开始着迷,一如既往,当我听到它时,我会感到脊背发凉。新京报:除了城堡之外,您在创作《撒旦探戈》之前工作的小镇蜥蜴也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Krasnohorkay:在我写 satantango 之前,它不仅是一个图书馆,而且我还烧过在写《萨坦戈》时我的手。那时,我已经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了,突然意识到整件事都很糟糕,就像任何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我不想写这样的书。于是我把手稿扔进了当时住的壁炉里的火里,然后我想到AKSelf我应该做出比这更大的牺牲——所以我也把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右手放在火上。毫无疑问,我的手心情不好,疼痛让我在房子旁边的小溪上跑上跑下好几个小时,无法控制,因为疼痛无法抗拒,我感觉自己快要模糊了。后来,疼痛依然不肯离开。我跑到一家诊所,请我坐下。我说我不能坐下,因为我一坐下,我肯定会痛。我的整个右臂都被烧伤了,愈合得很慢,当我写完这本书时,可怕的烧伤疤痕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是今天完全看不见。电影《撒旦探戈》中的匈牙利小酒馆。北京新闻,一位周游世界的文学公民:你为什么总是离开匈牙利?是为了在写作中寻找新鲜空气吗? Krasnohorkaj:当我想到匈牙利时,我总是需要新鲜空气。新京报:您会和其他匈牙利作家有交流吗,比如文化沙龙? Krasnohorkay:我不去沙龙,尤其是文学沙龙。我从那里什么也没拿走。写作,文学,对我来说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不应该用私人物品承载他人。几年来,每年一次,我都会邀请朋友来我家。但这些聚会的重要性不在于作家参加,而在于朋友的聚会。北京新闻:去年你在纽约待了整整一年,探寻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足迹,看来他对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时,你也被誉为“KA组合”克拉斯诺霍凯:梅尔维尔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白鲸》对我影响很大。但当时我大概十一岁了,小说中吸引我的不是鲸鱼,而是亚哈船长,我也像他一样思考自己,设身处地为他着想,那些日子、几周我独自站在房子的后院。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看到像亚哈船长那样的人在他的船上。当然,我读卡夫卡,感谢有机会进入我哥哥的朋友圈,他们比我大六岁,他们谈论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我看不懂卡夫卡的小说。我承认我害怕主角K,无论如何,我不想把自己当成他的。就在那时我读到 亚哈船长和我都理解他,所以他救了我。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不明白亚哈船长了。我对K有情感共鸣 新京报:你来过中国很多次了。 Krasnohorkay:是的,比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是我在南宋古城和乡村的一次旅行。那本书的书名是《天下毁灭悲哀》。在本书中,我正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谈谈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古代帝制时代的文化。谈话很有趣,我认识了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答案自然各不相同。 NaG -有人记得旅游业会对古代文化造成伤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人现在关心古代人留下的一切。作为一个欧洲人本身,我无疑会同意前一种观点。但我也发现了一些隐藏的、无法抹去的传统,这些传统就是维系着文化的。因为传统存在于人们自身之中。新京报:中国传统文化里,你喜欢李B人工智能。 Krasnohorkaj:我真的很喜欢李白。这是真实的。他不仅对我非常重要,而且他与唐代诗人一起被认为是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伟大诗人。我曾经喜欢过他,我和我的朋友、翻译家喻泽民一起去了李白走过的地方。我们参观了黄河沿岸的昔日大都市,游览了长江。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李白,以至于我追随他的脚步,想知道我是否可以见到他?我喜欢她的勇敢,我喜欢她的沉醉,月光,生命,分离,朋友——我喜欢她的节奏,无尽的能量,她流浪的本性——我喜欢李白和这个男人。当然,我只能想象基于伟大翻译的诗歌,但我预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是一首多么美妙的诗!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剧照,改编自拉斯洛小说《抵抗的忧郁》。人类需要的是一个假先知。北极新闻ng:接下来我们谈谈《撒旦探戈》的创作灵感? Krasnohorkay: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过着游牧生活。每三四个月我就会更换工作场所或居住在另一个城市或国家。我的工作之一是在一家乳品厂上夜班。我喜欢这份工作,晚上独自看守三百头牛。我总是在黎明时分跌跌撞撞地回家,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农舍里。有一次,小猪要被阉割了,主人让我不要躺着睡觉,让我做他的助手。我必须在露台上捡起两条前小猪腿。一个安静、可怕的男人,穿着长外套,长着一个大鼻子,跪在小猪的两条后腿之间,用一把锋利的刀给小猪做手术。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幕,缓缓抬起了头。我把头抬得越来越高,只要看到最高的屋顶。此刻,我看到天刚刚升起。太阳很大,呈棕色,就像是末日即将结束的征兆。世界开始了。我们完成工作后,我进去了,但我没有躺下,而是开始写“撒旦探戈”。因为那一刻的景象,整个“撒旦探戈”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完整了,我只需要把它写下来。新京报:《撒旦探戈》是一部长句复杂的小说。长句和短句之间有重要区别吗? Krasnohorkay:两种句子结构都有其原因。我个人喜欢旧的句子结构更有用,所以,当然,我想写长句子,这符合我的想法。一个人如何看待他选择的句子结构。人们不仅用长句子来思考,而且用单独的、无穷无尽的句子来思考。尤其是当他有特别的事情要说并且想要说服某人时。而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想让读者相信我写的东西。新京报:《撒旦探戈》中的伊利米亚什是一个带来希望并带领全村走向灭亡的骗子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么,你认为所有关于人类的集体假设,包括乌托邦和社会形式,都是一个甜蜜的骗局吗? Krasnohorkay:我只能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人们不需要先知,他们需要的是错误的先知——伊利米·阿什在《撒旦探戈》小说和同名电影中讲述了这一事实。新京报:你说这是一部悲喜剧。克拉斯诺霍凯:这对穷人来说是悲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要做什么,同时又是喜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要做什么。这既悲惨又好笑。它们只是最终方法的一部分。拉斯洛的《战争与战争》(War and War),1999年。故事开始从一个匈牙利小村庄转移到一座现代城市。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科林。他偶然在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古老的手稿,手稿讲述了一个回到奥德修斯的故事。在黑暗的生活中,科林原本打算自杀,交出自己的生命,但在此之前,他他计划将手稿带到纽约,并通过互联网将文字保存到手稿中,以便更多的人可以阅读。 《战争、警告》仍然采用KrasnoHornaj想要的结构方法。在第八章中,读者将回到之前的空间,将人性的绝望和死亡的沉重气息重新推迟到匈牙利的一家小酒馆。《新京报·书评周刊》对克拉斯诺霍尔凯·拉斯洛有专题报道。新闻:您的大量作品已被改编成贝拉·塔尔的电影,您也与银幕合作。结合起来,我们一起选择演员,一起选择地点,一起拍摄,简而言之,我们一起制作了《LAHat》。当然,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写剧本。塔尔写不出这种东西。毫无疑问,我需要自己做。我们所有的电影拍摄都是建立在友谊和合作的基础上的。我们首先是朋友,而不是同事。新京报:在贝拉·塔尔的长镜头中,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相同小说《撒旦探戈》也是如此,时间就像一个旋转的陷阱。你如何理解时间? CaratsNowholkay:塔尔,或者我们三个,不要把我的书改编成电影,我的书不需要调整,书已经结束了,这是最后的任务,不需要改编。我们需要制作的电影的灵感来自这些书,我写的书。塔尔是我作品的忠实粉丝,从 1985 年开始的二十五年里,他几乎拍了所有基于此的电影。我的作品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我在书中处理时间时,塔尔成功地在电影中实现了这一点。他想在电影中看到他在书中读到的同样的东西。时间重要的不是它的长度,而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他想在我们的帮助下拍摄发生了什么,世界的状况如何在漫长而无尽的时间内发生变化。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找到一种视觉表达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他在阅读时才知道、感觉到、随着书前进或静止不动。起身后,他在银幕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让观众有同样的感觉。重要的是这种状态,事物的状态,而不是情节,不是故事。北京新闻:你们之间没有矛盾吗?克拉斯诺霍尔凯:废话。我们是朋友,我们至今仍是朋友。友谊,如果是真正的友谊,就不会改变,更不会消亡。 “拉斯洛的 Seiobo”(2008)。克拉斯诺霍凯对新世纪的东方文化很感兴趣。除中国外,他还访问了蒙古、日本等国。 《西王母》是以日本神话中的西王母为背景的虚构小说。与前作相比,这部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共有17章,采用斐波那契数列进行统计。当章节从1章变成2584章时,似乎已经完成了更好的叙述。这源于基督教对东方佛陀的启示,寻求对抗和现代社会的解脱,其结果却是一场徒劳的悲剧,导致现代社会的毁灭。总的文学翻译与新京报创作:对于世界各地的读者来说,翻译是一个不一致的障碍。对于您小说的语言来说尤其如此。苏珊·桑塔格从未有机会阅读《撒旦探戈》的英文译本。据我所知,两年前它只被翻译成英文。将余泽民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可能会更加困难。 Krasnohorkay: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纽约遇见了苏珊,他知道小说《撒旦探戈》。他还可以阅读其他语言,当时这本书被翻译成德语和法语。我对他的分析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他写信给我:克拉斯诺霍纳伊是“匈牙利启示录的大师”。即使在今天,这听起来也有点圆滑。关于翻译,请允许我向我所有的 mgA 翻译人员表达我内心的共鸣,现在首先是余泽民,我信任的翻译。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多年以来,我都听他特别称赞过,说中国版的《撒旦探戈》有多好。我必须诚实面对。这本《撒旦探戈》,你在中国读的书是他的作品,不是我的。中国的《撒旦探戈》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写给他的。这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中文词汇。这些词是大家共同选择的。这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句子结构。这就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新风格!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无论谁喜欢这本书,我请你转向余泽民并向他问好。克拉斯诺霍凯与《SATTENTION》译者余泽民在咖啡馆里。他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新京报:这两年,大量匈牙利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在中国出版,比如马洛伊·桑德尔、克特兹·伊姆莱、埃斯特哈兹·彼得……您认为匈奴的独特之美是什么?世界上有哪些加里安文学?仅1000万人口,在文化高雅的中国很受读者欢迎。中文时间长了,还不太熟悉那些欧美读者。匈牙利语中可能隐藏着特殊而重要的秘密。因为匈牙利物产丰富,精致,所以说它脆弱易碎,就像一个精致的小瓷杯。它虽小,却有一种神秘的美。小而无与伦比-相信富有。大手粗暴笨拙地拿着瓷杯,需要小心谨慎。新京报:那么,您如何定位自己? Krasnohorkay:艺术家无法评判自己。他可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夸耀自己的作品;也许他很谦虚,就像塞缪尔·贝克特一样;也许他很谦虚。也许他因为自己的写作而感到自己是一个罪犯,就像卡夫卡一样;一个作家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价值,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的想法。如果“撒旦探戈”对一些读者来说,这将是最伟大的为我带来喜悦。要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儿童和成人、女人和男人、普通读者和训练有素的艺术家都可以从我写的书中得到一些东西,在这里和这里,这是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获得的最大成功。毫无疑问,其原因在于《撒旦探戈》,以它自己卑微的方式,就像世界上真正的文学杰作一样,继续围绕着同样的问题,围绕着人类尊严的问题,以加强对一个人的理解,无论他是读者还是演员:一个人应该拥有尊严,因为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尊严是人的尊严,因为无论如何,都不是人的尊严。 5月-集/公子、于泽民 编辑/李家瑜、张进、西西
1985年,31岁的克劳斯·瑙霍科伊·拉斯洛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撒旦探戈》,成为匈牙利文坛最受欢迎的作品。从此,他开始了他的创作之旅。 2017年,《撒旦探戈》版本出版。 《北京新闻周刊》曾对Klaus Nahuholkay Laszlo进行了长篇专访。以下为全文。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将授予匈牙利作家克劳斯·瑙霍尔凯·拉斯洛。匈牙利小说《KrasnoHornaj Laszlo》将卡夫卡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当我不读卡夫卡的时候,我就会想她。当我不读卡夫卡的时候,我就会想她。她走了一会儿后,我就拿着她的作品继续读。”他认为自己和卡夫卡的K有一些相似之处。和卡夫卡一样,他大学也学的是法律,纳格或许准备继承父亲的事业,但烦人的法律职业并不能满足他浪漫的灵魂。 1985年,31岁的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撒旦唐》于是,他一心一意,便成为了匈牙利文坛最著名的人物。此后,他开始专心写作,完成了七部长篇小说、链式结构令人惊叹的小说。克拉斯诺霍纳吉·拉斯洛,1954年出生,匈牙利作家。2015年布克国际奖获得者,代表作有《撒旦探戈》《反叛的忧郁》。 其风格特点是句子长而复杂,结构现代。然而,读者却很难走进他的小说。首先,语言是一个外部障碍。作为一门小语种的古老语言,匈牙利文学不仅与中国读者感觉相距甚远,而且与欧美读者的感觉也由来已久。最初享誉全球的《撒旦探戈》出自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改编。这部七小时的电影 被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知识分子成功捕捉到,这使得匈牙利文学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2013年,匈牙利诗人乔治·希奇将匈牙利语原著小说翻译成英文,让英美读者真正感受到了《撒旦探戈》的美妙。此后,克拉斯诺霍纳伊的作品一直被单独翻译,译者都是匈牙利诗人——他总能找到唯一合适的译者。 2015年,克拉斯诺霍纳伊荣获曼布克国际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匈牙利作家。今年,通过翻译余泽民,他终于有了该小说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但即使从匈牙利语转向中文,他的小说仍然在考验读者的耐心。除了长句形式之外,克拉斯诺霍尔凯的世界充满了人类的集体挫败、生命的无意义和悲伤的生物。任何人在阅读的过程中都会感觉自己成为了卡夫卡笔下的K,在指定的世界之外继续漫游,无法进入。卡夫卡曾经表演过他的短篇小说里描写了无数山洞里的人,用内心的突变来描述令他内心悲伤的噩梦般的场景;而克拉斯诺霍凯是一个卡皮谈话人物,他写马龙小说、外面的场景,以及人类集体的悲伤和沮丧。他把人们带到那座城堡,关上门,向他们展示了生活的徒劳,以及安徒生红鞋般的探戈舞步。采访与写作|新京报记者 龚照华 对话翻译| 《撒旦探戈》译者于泽民·克拉斯诺·霍纳吉·拉斯洛是一个需要深呼吸才能读得有气无力的名字——如他小说中的长句,获得无穷的分量。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他是一位非常熟悉的作家,《撒旦探戈》也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但事实上,他早已在文坛闯荡,也多次来过中国。他对李白和儒家经典的理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更深的卡亚。他还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好丘”,意思是美丽的山丘,以及他对孔子的热爱。克拉斯诺霍卡伊·拉斯洛(Krasnohorkaj Laszlo)1954年1月5日出生于匈牙利久洛小镇。他的小说经常以匈牙利小镇的酒馆为场景。但单一国家并不能满足他的愿景。在完成他的处女作《撒旦探戈》两年后,他带着奖金离开了匈牙利,开始了他作为世界公民的旅程。首先是西德、法国、西班牙,然后是美国、意大利、希腊,最后是日本和中国。他在中国向游客讲述李白,并在纽约追随梅尔维尔的脚步。克拉斯诺霍凯目前住在德国柏林的家中。 《设定撒旦探戈》:【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卡伊·拉兹洛 译者:于泽民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7年7月《撒旦探戈》之前的写作和烧录 新京报:斯洛伐克有一座和你同姓的城堡。你认为你和它有联系吗? (城堡毁于一场大火几年前)克拉斯诺霍卡:一座匈牙利城堡位于斯洛伐克的克拉斯诺霍卡。这是一座有近八百年历史的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它被划分为匈牙利领土的一部分并被割让给斯洛伐克时,这座建筑成为了一个象征,有人写了一首关于它的歌曲,在匈牙利全国闻名,但那是一首可怕的歌曲,每次听到它,我都会脊背发凉。然而,在我们家,我的祖父很喜欢这首歌,并在一家小酒馆里整天唱这首歌,并决定用这个地方作为他家族的名字。这是我们以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名字,而现在,所有具有政治敏感度的出租车司机——一旦他们在向我开具发票时发现了我的名字——就开始着迷,一如既往,当我听到它时,我会感到脊背发凉。新京报:除了城堡之外,您在创作《撒旦探戈》之前工作的小镇蜥蜴也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Krasnohorkay:在我写 satantango 之前,它不仅是一个图书馆,而且我还烧过在写《萨坦戈》时我的手。那时,我已经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了,突然意识到整件事都很糟糕,就像任何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我不想写这样的书。于是我把手稿扔进了当时住的壁炉里的火里,然后我想到AKSelf我应该做出比这更大的牺牲——所以我也把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右手放在火上。毫无疑问,我的手心情不好,疼痛让我在房子旁边的小溪上跑上跑下好几个小时,无法控制,因为疼痛无法抗拒,我感觉自己快要模糊了。后来,疼痛依然不肯离开。我跑到一家诊所,请我坐下。我说我不能坐下,因为我一坐下,我肯定会痛。我的整个右臂都被烧伤了,愈合得很慢,当我写完这本书时,可怕的烧伤疤痕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是今天完全看不见。电影《撒旦探戈》中的匈牙利小酒馆。北京新闻,一位周游世界的文学公民:你为什么总是离开匈牙利?是为了在写作中寻找新鲜空气吗? Krasnohorkaj:当我想到匈牙利时,我总是需要新鲜空气。新京报:您会和其他匈牙利作家有交流吗,比如文化沙龙? Krasnohorkay:我不去沙龙,尤其是文学沙龙。我从那里什么也没拿走。写作,文学,对我来说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不应该用私人物品承载他人。几年来,每年一次,我都会邀请朋友来我家。但这些聚会的重要性不在于作家参加,而在于朋友的聚会。北京新闻:去年你在纽约待了整整一年,探寻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足迹,看来他对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时,你也被誉为“KA组合”克拉斯诺霍凯:梅尔维尔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白鲸》对我影响很大。但当时我大概十一岁了,小说中吸引我的不是鲸鱼,而是亚哈船长,我也像他一样思考自己,设身处地为他着想,那些日子、几周我独自站在房子的后院。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看到像亚哈船长那样的人在他的船上。当然,我读卡夫卡,感谢有机会进入我哥哥的朋友圈,他们比我大六岁,他们谈论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我看不懂卡夫卡的小说。我承认我害怕主角K,无论如何,我不想把自己当成他的。就在那时我读到 亚哈船长和我都理解他,所以他救了我。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不明白亚哈船长了。我对K有情感共鸣 新京报:你来过中国很多次了。 Krasnohorkay:是的,比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是我在南宋古城和乡村的一次旅行。那本书的书名是《天下毁灭悲哀》。在本书中,我正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谈谈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古代帝制时代的文化。谈话很有趣,我认识了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答案自然各不相同。 NaG -有人记得旅游业会对古代文化造成伤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人现在关心古代人留下的一切。作为一个欧洲人本身,我无疑会同意前一种观点。但我也发现了一些隐藏的、无法抹去的传统,这些传统就是维系着文化的。因为传统存在于人们自身之中。新京报:中国传统文化里,你喜欢李B人工智能。 Krasnohorkaj:我真的很喜欢李白。这是真实的。他不仅对我非常重要,而且他与唐代诗人一起被认为是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伟大诗人。我曾经喜欢过他,我和我的朋友、翻译家喻泽民一起去了李白走过的地方。我们参观了黄河沿岸的昔日大都市,游览了长江。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李白,以至于我追随他的脚步,想知道我是否可以见到他?我喜欢她的勇敢,我喜欢她的沉醉,月光,生命,分离,朋友——我喜欢她的节奏,无尽的能量,她流浪的本性——我喜欢李白和这个男人。当然,我只能想象基于伟大翻译的诗歌,但我预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是一首多么美妙的诗!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剧照,改编自拉斯洛小说《抵抗的忧郁》。人类需要的是一个假先知。北极新闻ng:接下来我们谈谈《撒旦探戈》的创作灵感? Krasnohorkay: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过着游牧生活。每三四个月我就会更换工作场所或居住在另一个城市或国家。我的工作之一是在一家乳品厂上夜班。我喜欢这份工作,晚上独自看守三百头牛。我总是在黎明时分跌跌撞撞地回家,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农舍里。有一次,小猪要被阉割了,主人让我不要躺着睡觉,让我做他的助手。我必须在露台上捡起两条前小猪腿。一个安静、可怕的男人,穿着长外套,长着一个大鼻子,跪在小猪的两条后腿之间,用一把锋利的刀给小猪做手术。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幕,缓缓抬起了头。我把头抬得越来越高,只要看到最高的屋顶。此刻,我看到天刚刚升起。太阳很大,呈棕色,就像是末日即将结束的征兆。世界开始了。我们完成工作后,我进去了,但我没有躺下,而是开始写“撒旦探戈”。因为那一刻的景象,整个“撒旦探戈”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完整了,我只需要把它写下来。新京报:《撒旦探戈》是一部长句复杂的小说。长句和短句之间有重要区别吗? Krasnohorkay:两种句子结构都有其原因。我个人喜欢旧的句子结构更有用,所以,当然,我想写长句子,这符合我的想法。一个人如何看待他选择的句子结构。人们不仅用长句子来思考,而且用单独的、无穷无尽的句子来思考。尤其是当他有特别的事情要说并且想要说服某人时。而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想让读者相信我写的东西。新京报:《撒旦探戈》中的伊利米亚什是一个带来希望并带领全村走向灭亡的骗子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么,你认为所有关于人类的集体假设,包括乌托邦和社会形式,都是一个甜蜜的骗局吗? Krasnohorkay:我只能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人们不需要先知,他们需要的是错误的先知——伊利米·阿什在《撒旦探戈》小说和同名电影中讲述了这一事实。新京报:你说这是一部悲喜剧。克拉斯诺霍凯:这对穷人来说是悲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要做什么,同时又是喜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要做什么。这既悲惨又好笑。它们只是最终方法的一部分。拉斯洛的《战争与战争》(War and War),1999年。故事开始从一个匈牙利小村庄转移到一座现代城市。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科林。他偶然在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古老的手稿,手稿讲述了一个回到奥德修斯的故事。在黑暗的生活中,科林原本打算自杀,交出自己的生命,但在此之前,他他计划将手稿带到纽约,并通过互联网将文字保存到手稿中,以便更多的人可以阅读。 《战争、警告》仍然采用KrasnoHornaj想要的结构方法。在第八章中,读者将回到之前的空间,将人性的绝望和死亡的沉重气息重新推迟到匈牙利的一家小酒馆。《新京报·书评周刊》对克拉斯诺霍尔凯·拉斯洛有专题报道。新闻:您的大量作品已被改编成贝拉·塔尔的电影,您也与银幕合作。结合起来,我们一起选择演员,一起选择地点,一起拍摄,简而言之,我们一起制作了《LAHat》。当然,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写剧本。塔尔写不出这种东西。毫无疑问,我需要自己做。我们所有的电影拍摄都是建立在友谊和合作的基础上的。我们首先是朋友,而不是同事。新京报:在贝拉·塔尔的长镜头中,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相同小说《撒旦探戈》也是如此,时间就像一个旋转的陷阱。你如何理解时间? CaratsNowholkay:塔尔,或者我们三个,不要把我的书改编成电影,我的书不需要调整,书已经结束了,这是最后的任务,不需要改编。我们需要制作的电影的灵感来自这些书,我写的书。塔尔是我作品的忠实粉丝,从 1985 年开始的二十五年里,他几乎拍了所有基于此的电影。我的作品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我在书中处理时间时,塔尔成功地在电影中实现了这一点。他想在电影中看到他在书中读到的同样的东西。时间重要的不是它的长度,而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他想在我们的帮助下拍摄发生了什么,世界的状况如何在漫长而无尽的时间内发生变化。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找到一种视觉表达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他在阅读时才知道、感觉到、随着书前进或静止不动。起身后,他在银幕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让观众有同样的感觉。重要的是这种状态,事物的状态,而不是情节,不是故事。北京新闻:你们之间没有矛盾吗?克拉斯诺霍尔凯:废话。我们是朋友,我们至今仍是朋友。友谊,如果是真正的友谊,就不会改变,更不会消亡。 “拉斯洛的 Seiobo”(2008)。克拉斯诺霍凯对新世纪的东方文化很感兴趣。除中国外,他还访问了蒙古、日本等国。 《西王母》是以日本神话中的西王母为背景的虚构小说。与前作相比,这部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共有17章,采用斐波那契数列进行统计。当章节从1章变成2584章时,似乎已经完成了更好的叙述。这源于基督教对东方佛陀的启示,寻求对抗和现代社会的解脱,其结果却是一场徒劳的悲剧,导致现代社会的毁灭。总的文学翻译与新京报创作:对于世界各地的读者来说,翻译是一个不一致的障碍。对于您小说的语言来说尤其如此。苏珊·桑塔格从未有机会阅读《撒旦探戈》的英文译本。据我所知,两年前它只被翻译成英文。将余泽民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可能会更加困难。 Krasnohorkay: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纽约遇见了苏珊,他知道小说《撒旦探戈》。他还可以阅读其他语言,当时这本书被翻译成德语和法语。我对他的分析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他写信给我:克拉斯诺霍纳伊是“匈牙利启示录的大师”。即使在今天,这听起来也有点圆滑。关于翻译,请允许我向我所有的 mgA 翻译人员表达我内心的共鸣,现在首先是余泽民,我信任的翻译。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多年以来,我都听他特别称赞过,说中国版的《撒旦探戈》有多好。我必须诚实面对。这本《撒旦探戈》,你在中国读的书是他的作品,不是我的。中国的《撒旦探戈》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写给他的。这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中文词汇。这些词是大家共同选择的。这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句子结构。这就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新风格!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无论谁喜欢这本书,我请你转向余泽民并向他问好。克拉斯诺霍凯与《SATTENTION》译者余泽民在咖啡馆里。他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新京报:这两年,大量匈牙利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在中国出版,比如马洛伊·桑德尔、克特兹·伊姆莱、埃斯特哈兹·彼得……您认为匈奴的独特之美是什么?世界上有哪些加里安文学?仅1000万人口,在文化高雅的中国很受读者欢迎。中文时间长了,还不太熟悉那些欧美读者。匈牙利语中可能隐藏着特殊而重要的秘密。因为匈牙利物产丰富,精致,所以说它脆弱易碎,就像一个精致的小瓷杯。它虽小,却有一种神秘的美。小而无与伦比-相信富有。大手粗暴笨拙地拿着瓷杯,需要小心谨慎。新京报:那么,您如何定位自己? Krasnohorkay:艺术家无法评判自己。他可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夸耀自己的作品;也许他很谦虚,就像塞缪尔·贝克特一样;也许他很谦虚。也许他因为自己的写作而感到自己是一个罪犯,就像卡夫卡一样;一个作家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价值,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的想法。如果“撒旦探戈”对一些读者来说,这将是最伟大的为我带来喜悦。要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儿童和成人、女人和男人、普通读者和训练有素的艺术家都可以从我写的书中得到一些东西,在这里和这里,这是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获得的最大成功。毫无疑问,其原因在于《撒旦探戈》,以它自己卑微的方式,就像世界上真正的文学杰作一样,继续围绕着同样的问题,围绕着人类尊严的问题,以加强对一个人的理解,无论他是读者还是演员:一个人应该拥有尊严,因为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尊严是人的尊严,因为无论如何,都不是人的尊严。 5月-集/公子、于泽民 编辑/李家瑜、张进、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