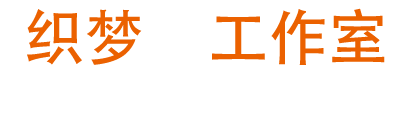人类社会中“不将人类视为人类”的问题:哲学
- 编辑:皇冠APP官方下载 -人类社会中“不将人类视为人类”的问题: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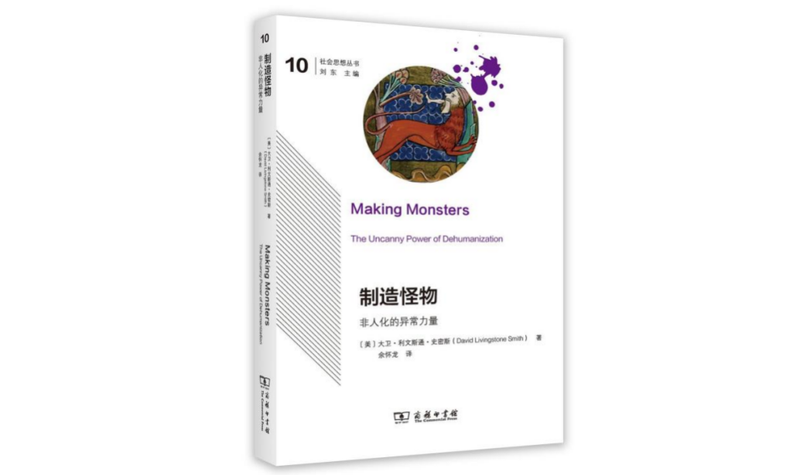 如何定义“人”?在哲学层面,这个抽象问题的答案无疑列出了许多理论和理论。当我们转向一天 - 一天的生活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人们很少定义“人”,他们也总是总是对“人”是什么表达自己的看法。例如,当人们谈论生活的感觉时,他们以“人们,最重要的是幸福”开始。它是对“人”的描述,但它定义了救赎的目标和含义。与“人”是什么或人们对某事表达不愉快性和某种现象(例如“人们可以做到的?”)时,什么是什么直接关系。通过重新尊重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差异,这是定义“人”的时尚方法。当然,人类也是动物。当第一批人撤离野蛮人并进入文明状态时,“人类”出现了,动物中出现了差异。作为人类,哼ANS可能不会对其类型提供暴力,而是被允许杀死动物。在“非人性化”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中,研究人员认为,人性中有一系列心理机制限制了人们的暴力行为,因此,对他人的暴力行为的过程是其他各方“去除人”的过程。仅通过将另一方视为“不是人类”(“不将人为人类”的问题),就可以打破心理机制的强烈障碍。当然,最终行为本身就是“不是人类”的自然。哲学家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以“非人性化”的研究而闻名,他将其描述为“制作怪物”。黑人和犹太人曾经被视为“怪物”作为集体图片。以下内容是,在出版商的许可下,它是从“制造怪物”一书中暴露的,这是该集合谈论来自自然暴力行为的机制。摘录被删除,标题来自段落,可以在原始书中找到评论。最初带有-set | [我们]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制造怪物”五月 - 塞特:[我们]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翻译:Yu Huailong翻译:商业出版社2025年6月,当我写这些话时,自然界的和解与冲突,我坐在地板上,俯瞰着新英格兰的家后面的大树林。两只美丽的红尾鹰在一棵高大的树上见证了一棵高大的树,每次我看到潜水时,都会带着爪子,爪子或田鼠,用爪子到栖息,撕下活的动物,然后猛烈地吃掉它们。在附近,我看到蜻蜓在院子里飞。这是一个很好的景象,但我知道在空中表演的杂技演员是凶猛的掠食者,微型杀害了寻找蚊子和其他昆虫的机器。蜻蜓食用的许多蚊子都是圆形的,因为他们胃中的血来自美国漫游的美国。在附近,一群小蚂蚁博士在我脚下的地板上搅动了一个扭曲的毛毛虫,然后将其带到巢中,将其吞下。来自“LeRègneAnimal,2023”的剧照。大自然不好。如果Swhere Life继续彼此吃饭,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令人恐惧的地方。许多动物生活在其他动物中,甚至温和的植物都在毁灭性和进食植物。如果植物能哭泣,它们肯定会继续发出噪音。一些生物已经与受害者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播种种子,摄食生物可以获得相应的卡路里。但是对于大多数其他生物来说,自然敌人的存在意味着剥削或破坏。这就是为什么Arthur Schopenhauer将大自然描述为“充满酷刑和痛苦的游乐场,生物只能通过互相绑架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每只坏动物都是成千上万的其他海上的活着的坟墓,他们只能通过互相喂食来继续生活……并经历痛苦的痛苦……HS”。或者,正如Philip Kitcher指出的那样,“痛苦不是生活机会中发生的事情,而是保留的。 “暴力是生活的状态。智人也不例外。像使用动物羽毛和纤维在制作衣服,木头,角和种子制造最终将用于娱乐的工具和装饰品一样,我们杀死牺牲品来将它们杀死,以将动物视为将动物视为食物,鸡蛋,鸡蛋和牛奶,牛奶和牛奶,耕作和耕种工具,而是在不适合其他工具。如果他们不严格陷入大多数社交动物的态度,那么在攻击和克制之间取得了适当的平衡,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进化使他们有一系列的本能来应对这种平衡。 - 他们被允许消除生命。他们只是遵循本能。但是我们与同性恋者不同。我们不依赖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倾向于自然,而我们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多的行为机构。我们应该做出选择,并被迫找到理由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对动物的状况的解释,我们的祖先面临着为什么有些生物可以杀死的挑战,而不是其他生物?无论他们有多深,他们都需要推理声明,这是对谋杀政策的解释。在当今的一些食品收集文化中,人们发现了这样的推理陈述(这可能是狩猎文化的共同点):人们和受害者之间作为猎人有伙伴关系。动物出现在猎人面前,因为他们想狩猎。因此,被杀死的人类是为了满足动物的愿望而被杀死的动物,而动物将其赋予生命,而不是人类被人类带走。格雷厄姆·哈维(Graham Harvey)宗教研究学者写道:在某些地方,萨满巫师的一项工作是说服猎人发现并为人类的利益而屈服的动物。换句话说,萨满说服动物和人们狩猎和狩猎都是牺牲。死亡是不愉快的,通常没有道理。但是牺牲是圣洁的,超越的,而且不仅仅是生命。因此,萨满可能需要找到别人隐藏的东西:远处的动物。当他们知道目标动物在哪里时,萨满通常会试图说服隐藏的受害者见猎人并说服比克蒂马放弃生命。在文化上,萨满表达了对受害者的适当尊重,并承诺在受害者死后和之后采取进一步的礼貌行为。在某些版本中,被杀死后,他们的灵魂将继续存在,一定会得到安慰。在其他版本中,它们再次与其他动物相同,再次与无尽的多变一起H死亡和重生。纪录片“ Earthlings,2005”反映了动物的杀戮。当然,猎人知道动物试图不杀死和恐惧那些想杀死它们的人。每个猎人都知道,被尸体刺穿的动物在死亡之前会遭受痛苦。动物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想法,旨在使他们的狩猎人士合法。这是一种信念,即该功能是使一个群体(即人类社会)受益,并牺牲另一个群体(被人类剥削和杀死的非人类动物群体)。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信念的运作是“被压迫”的动物的运作。您可能会发现,不建议使用“欺凌”一词来描述我们与非人类生物的关系。当然,您可以想象这个词仅适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但是,您的想法与我在第9章中解释的分层框架的概念不一致。”只有人们被压迫,“这种直觉是基于一个深厚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偏见,我们将比其他生物更能占据宇宙依从性的地位。在某些时候,婚姻动物的出现,agrikultura and Class Society的外观,Agrikultura and Class Society的外观,谋杀的新概念是如此强大的概念。物种对其他生物的合法性被认为是在“存在的巨大链条”中杀死和食用的,因为它们不是人类的杀戮和食物。针对其他生物体的暴力S,从而为人类的态度提供系统的支持。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巨大生存链”概念可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控制人类思维的原因。生命的饲料和自然等级制度的概念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控制我们依靠用于生殖和安全的暴力行为。超级社交我们是如此的社交动物。实际上,没有灵长类动物,没有哺乳动物,可以具有如此高的社会化,例如智人。要生活在高度社交群体中,我们必须有可能适应社会关系的想法。研究表明,在孤独的孤独中,囚犯提出的国家包括“焦虑,清除,严重的敏感性,压倒性,认知失效,没有幻觉,幻觉,kon的控制,易怒,侵略性,愤怒,愤怒,偏执,绝望,情感跌倒,情感衰落,自我损害,自我伤害,自杀和自杀。大卫·休姆(David Hume)说:“我们将月球视为人的面孔,云云为军队,善意和善意,一切根据自然的激情受到伤害或享受我们的一切。”暴力史(2005)。社会应避免对社区成员进行致命或致命的攻击,否则社区将不存在。因此,人类的超社会性阻止了人们之间的暴力行为。这是可以的合作。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对人类暴力的广泛研究中写道:“人们的主要态度是互相关注并吸引彼此的身体和情感色调的节奏。”柯林斯认为,这些过程是无意识的,自发的,并且有吸引力。最愉快的人类活动是,人类被微交流的独特节奏所吸引:共同的语气,平稳的对话,对笑声中的默认面的理解,大多数人的热情,都是性唤醒。通常,这些过程构成了一种互动仪式,至少现在时刻产生一种主体间和道德统一感。脸上的冲突很难首先发生,因为它违反了常识,身体和精神满意度的意义。 ...有一个明显的障碍可以防止我们陷入暴力对抗。它违反了人民的生理定律,也就是说,它违反了人类无关紧要的团结与合作的趋势。反法西斯电影《美丽的生活》(LaVitaèBella,1997年)。暴力对抗的强烈形式是身体暴力,最严重的是杀人。因此,如果柯林斯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对社会统一的偏好将不可避免地构成一个如何激发军事军事战斗能力的问题。确实是这样。 1947年,美国陆军历史学家S. L. A. Marshall发表了一件远程人类的作品,尤其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对抗:与火对抗:战斗命令的问题。这本书强调了一本激进的美国军事训练改革。他解释了本书上面的问题。战斗结束后,士兵们立即士兵们,他发现许多步兵在射击中发现了困难,而不是在设备上,而是在心理困难中。他说,这些采访使他相信士兵常常不允许自己使用致命武器,因为“总的来说,普通武器,即那些不知道反对谋杀同胞的斗争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逃脱战争,他们将不会采取行动来杀害人民。”社会化:他由家人,宗教,教育,道德标准和社会目标塑造。我们应该考虑一个事实,即如果禁止和不可接受,他是来自文明社会的事实。她对虐待的恐惧是如此强大,非常深,很长时间,她母亲的牛奶对她的情感组成的一部分的所有影响他正常的人。当他参加战斗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尽管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的束缚,但他的手指停止了扳机。因为这是一个情感上的障碍,而不是提供障碍,因此不能通过提供“谋杀或谋杀”等意识来消除这种障碍。马歇尔对士兵对谋杀的心理抵抗的解释与正统的观点一致,即他一直在努力。这种观点认为,除了某些自然条件外,所有人类行为都是通过适应环境来学习的。抑制暴力的心理机制来自心理学发展的一些证据表明,婴儿天生具有合作和无私的精神。心理学教授兼战争资深人士戴维·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引起了马歇尔思想的更多关注。他不同意马歇尔对士兵为什么经常遇到困难的解释。他贝尔ieves人是为了防止杀死他人的行为。格罗斯曼(Grossman)认为这种抵抗力非常强大。来自“年轻人”的静止图(2019)。尽管马歇尔(Marshall)和格罗斯曼(Grossman)的作品都是理解的,但毕竟它们不是学术作品,而给他们的证据也更好。此外,马歇尔关于士兵对杀害的抵抗的说法得到了强烈批评。但是,他们与其他学者相似。另一个例子由奥地利有影响力的研究IrenäusEibl-Eibesfeldt提供。他认为,萨皮人天生就被谋杀(tötungshemmungen)本能 - 一种生物学抑制杀害类似物种的生物学抑制:“侵略性人类行为有效地受到许多系统发育适应的有效控制……我们天生具有抑制积极行为的能力。”来自“ Apocalypto”(2006)的剧照。心理热的库什曼及其同事描述了人们如何在题为“模拟的论文中防止侵略性行为他们进行的一项实验记录了本文,以确定预防暴力是否仅基于受害者的同情或偶尔以避免暴力行为。捡起巨石并从物体衬衫的袖子上伸出来,第三个是用逼真的玩具枪的“射击”。知道不一个人在实验中受到伤害,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疼痛迹象,尤其是当他们自己做这些行为而不是看别人的行为时。实验表明,这是暴力本身,而不是道德的后果,这引起了厌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动不受有害后果的影响,而是意味着仅仅关注道德同情并不能说明整个故事。库什曼和同事得出结论:“对危害行为的自发反应反应可能会解释其他令人困惑的人类行为。在战场和虚假的道德判断中,人们拒绝直接伤害,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可以挽救许多生命。研究很多。对行为的反应是分开的SE观察意味着普通人具有一种心理机制,可以自动调整侵略性行为,从而自发地操作并间接控制意识。这种机制可以是自然的,是由基因提到的,也可以是获得的,也可能是我们可以快速学习的东西。存在心理机制,它具有抑制人际暴力的作用。
如何定义“人”?在哲学层面,这个抽象问题的答案无疑列出了许多理论和理论。当我们转向一天 - 一天的生活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人们很少定义“人”,他们也总是总是对“人”是什么表达自己的看法。例如,当人们谈论生活的感觉时,他们以“人们,最重要的是幸福”开始。它是对“人”的描述,但它定义了救赎的目标和含义。与“人”是什么或人们对某事表达不愉快性和某种现象(例如“人们可以做到的?”)时,什么是什么直接关系。通过重新尊重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差异,这是定义“人”的时尚方法。当然,人类也是动物。当第一批人撤离野蛮人并进入文明状态时,“人类”出现了,动物中出现了差异。作为人类,哼ANS可能不会对其类型提供暴力,而是被允许杀死动物。在“非人性化”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中,研究人员认为,人性中有一系列心理机制限制了人们的暴力行为,因此,对他人的暴力行为的过程是其他各方“去除人”的过程。仅通过将另一方视为“不是人类”(“不将人为人类”的问题),就可以打破心理机制的强烈障碍。当然,最终行为本身就是“不是人类”的自然。哲学家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以“非人性化”的研究而闻名,他将其描述为“制作怪物”。黑人和犹太人曾经被视为“怪物”作为集体图片。以下内容是,在出版商的许可下,它是从“制造怪物”一书中暴露的,这是该集合谈论来自自然暴力行为的机制。摘录被删除,标题来自段落,可以在原始书中找到评论。最初带有-set | [我们]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制造怪物”五月 - 塞特:[我们]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翻译:Yu Huailong翻译:商业出版社2025年6月,当我写这些话时,自然界的和解与冲突,我坐在地板上,俯瞰着新英格兰的家后面的大树林。两只美丽的红尾鹰在一棵高大的树上见证了一棵高大的树,每次我看到潜水时,都会带着爪子,爪子或田鼠,用爪子到栖息,撕下活的动物,然后猛烈地吃掉它们。在附近,我看到蜻蜓在院子里飞。这是一个很好的景象,但我知道在空中表演的杂技演员是凶猛的掠食者,微型杀害了寻找蚊子和其他昆虫的机器。蜻蜓食用的许多蚊子都是圆形的,因为他们胃中的血来自美国漫游的美国。在附近,一群小蚂蚁博士在我脚下的地板上搅动了一个扭曲的毛毛虫,然后将其带到巢中,将其吞下。来自“LeRègneAnimal,2023”的剧照。大自然不好。如果Swhere Life继续彼此吃饭,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令人恐惧的地方。许多动物生活在其他动物中,甚至温和的植物都在毁灭性和进食植物。如果植物能哭泣,它们肯定会继续发出噪音。一些生物已经与受害者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播种种子,摄食生物可以获得相应的卡路里。但是对于大多数其他生物来说,自然敌人的存在意味着剥削或破坏。这就是为什么Arthur Schopenhauer将大自然描述为“充满酷刑和痛苦的游乐场,生物只能通过互相绑架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每只坏动物都是成千上万的其他海上的活着的坟墓,他们只能通过互相喂食来继续生活……并经历痛苦的痛苦……HS”。或者,正如Philip Kitcher指出的那样,“痛苦不是生活机会中发生的事情,而是保留的。 “暴力是生活的状态。智人也不例外。像使用动物羽毛和纤维在制作衣服,木头,角和种子制造最终将用于娱乐的工具和装饰品一样,我们杀死牺牲品来将它们杀死,以将动物视为将动物视为食物,鸡蛋,鸡蛋和牛奶,牛奶和牛奶,耕作和耕种工具,而是在不适合其他工具。如果他们不严格陷入大多数社交动物的态度,那么在攻击和克制之间取得了适当的平衡,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进化使他们有一系列的本能来应对这种平衡。 - 他们被允许消除生命。他们只是遵循本能。但是我们与同性恋者不同。我们不依赖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倾向于自然,而我们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多的行为机构。我们应该做出选择,并被迫找到理由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对动物的状况的解释,我们的祖先面临着为什么有些生物可以杀死的挑战,而不是其他生物?无论他们有多深,他们都需要推理声明,这是对谋杀政策的解释。在当今的一些食品收集文化中,人们发现了这样的推理陈述(这可能是狩猎文化的共同点):人们和受害者之间作为猎人有伙伴关系。动物出现在猎人面前,因为他们想狩猎。因此,被杀死的人类是为了满足动物的愿望而被杀死的动物,而动物将其赋予生命,而不是人类被人类带走。格雷厄姆·哈维(Graham Harvey)宗教研究学者写道:在某些地方,萨满巫师的一项工作是说服猎人发现并为人类的利益而屈服的动物。换句话说,萨满说服动物和人们狩猎和狩猎都是牺牲。死亡是不愉快的,通常没有道理。但是牺牲是圣洁的,超越的,而且不仅仅是生命。因此,萨满可能需要找到别人隐藏的东西:远处的动物。当他们知道目标动物在哪里时,萨满通常会试图说服隐藏的受害者见猎人并说服比克蒂马放弃生命。在文化上,萨满表达了对受害者的适当尊重,并承诺在受害者死后和之后采取进一步的礼貌行为。在某些版本中,被杀死后,他们的灵魂将继续存在,一定会得到安慰。在其他版本中,它们再次与其他动物相同,再次与无尽的多变一起H死亡和重生。纪录片“ Earthlings,2005”反映了动物的杀戮。当然,猎人知道动物试图不杀死和恐惧那些想杀死它们的人。每个猎人都知道,被尸体刺穿的动物在死亡之前会遭受痛苦。动物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想法,旨在使他们的狩猎人士合法。这是一种信念,即该功能是使一个群体(即人类社会)受益,并牺牲另一个群体(被人类剥削和杀死的非人类动物群体)。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信念的运作是“被压迫”的动物的运作。您可能会发现,不建议使用“欺凌”一词来描述我们与非人类生物的关系。当然,您可以想象这个词仅适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但是,您的想法与我在第9章中解释的分层框架的概念不一致。”只有人们被压迫,“这种直觉是基于一个深厚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偏见,我们将比其他生物更能占据宇宙依从性的地位。在某些时候,婚姻动物的出现,agrikultura and Class Society的外观,Agrikultura and Class Society的外观,谋杀的新概念是如此强大的概念。物种对其他生物的合法性被认为是在“存在的巨大链条”中杀死和食用的,因为它们不是人类的杀戮和食物。针对其他生物体的暴力S,从而为人类的态度提供系统的支持。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巨大生存链”概念可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控制人类思维的原因。生命的饲料和自然等级制度的概念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控制我们依靠用于生殖和安全的暴力行为。超级社交我们是如此的社交动物。实际上,没有灵长类动物,没有哺乳动物,可以具有如此高的社会化,例如智人。要生活在高度社交群体中,我们必须有可能适应社会关系的想法。研究表明,在孤独的孤独中,囚犯提出的国家包括“焦虑,清除,严重的敏感性,压倒性,认知失效,没有幻觉,幻觉,kon的控制,易怒,侵略性,愤怒,愤怒,偏执,绝望,情感跌倒,情感衰落,自我损害,自我伤害,自杀和自杀。大卫·休姆(David Hume)说:“我们将月球视为人的面孔,云云为军队,善意和善意,一切根据自然的激情受到伤害或享受我们的一切。”暴力史(2005)。社会应避免对社区成员进行致命或致命的攻击,否则社区将不存在。因此,人类的超社会性阻止了人们之间的暴力行为。这是可以的合作。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对人类暴力的广泛研究中写道:“人们的主要态度是互相关注并吸引彼此的身体和情感色调的节奏。”柯林斯认为,这些过程是无意识的,自发的,并且有吸引力。最愉快的人类活动是,人类被微交流的独特节奏所吸引:共同的语气,平稳的对话,对笑声中的默认面的理解,大多数人的热情,都是性唤醒。通常,这些过程构成了一种互动仪式,至少现在时刻产生一种主体间和道德统一感。脸上的冲突很难首先发生,因为它违反了常识,身体和精神满意度的意义。 ...有一个明显的障碍可以防止我们陷入暴力对抗。它违反了人民的生理定律,也就是说,它违反了人类无关紧要的团结与合作的趋势。反法西斯电影《美丽的生活》(LaVitaèBella,1997年)。暴力对抗的强烈形式是身体暴力,最严重的是杀人。因此,如果柯林斯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对社会统一的偏好将不可避免地构成一个如何激发军事军事战斗能力的问题。确实是这样。 1947年,美国陆军历史学家S. L. A. Marshall发表了一件远程人类的作品,尤其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对抗:与火对抗:战斗命令的问题。这本书强调了一本激进的美国军事训练改革。他解释了本书上面的问题。战斗结束后,士兵们立即士兵们,他发现许多步兵在射击中发现了困难,而不是在设备上,而是在心理困难中。他说,这些采访使他相信士兵常常不允许自己使用致命武器,因为“总的来说,普通武器,即那些不知道反对谋杀同胞的斗争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逃脱战争,他们将不会采取行动来杀害人民。”社会化:他由家人,宗教,教育,道德标准和社会目标塑造。我们应该考虑一个事实,即如果禁止和不可接受,他是来自文明社会的事实。她对虐待的恐惧是如此强大,非常深,很长时间,她母亲的牛奶对她的情感组成的一部分的所有影响他正常的人。当他参加战斗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尽管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的束缚,但他的手指停止了扳机。因为这是一个情感上的障碍,而不是提供障碍,因此不能通过提供“谋杀或谋杀”等意识来消除这种障碍。马歇尔对士兵对谋杀的心理抵抗的解释与正统的观点一致,即他一直在努力。这种观点认为,除了某些自然条件外,所有人类行为都是通过适应环境来学习的。抑制暴力的心理机制来自心理学发展的一些证据表明,婴儿天生具有合作和无私的精神。心理学教授兼战争资深人士戴维·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引起了马歇尔思想的更多关注。他不同意马歇尔对士兵为什么经常遇到困难的解释。他贝尔ieves人是为了防止杀死他人的行为。格罗斯曼(Grossman)认为这种抵抗力非常强大。来自“年轻人”的静止图(2019)。尽管马歇尔(Marshall)和格罗斯曼(Grossman)的作品都是理解的,但毕竟它们不是学术作品,而给他们的证据也更好。此外,马歇尔关于士兵对杀害的抵抗的说法得到了强烈批评。但是,他们与其他学者相似。另一个例子由奥地利有影响力的研究IrenäusEibl-Eibesfeldt提供。他认为,萨皮人天生就被谋杀(tötungshemmungen)本能 - 一种生物学抑制杀害类似物种的生物学抑制:“侵略性人类行为有效地受到许多系统发育适应的有效控制……我们天生具有抑制积极行为的能力。”来自“ Apocalypto”(2006)的剧照。心理热的库什曼及其同事描述了人们如何在题为“模拟的论文中防止侵略性行为他们进行的一项实验记录了本文,以确定预防暴力是否仅基于受害者的同情或偶尔以避免暴力行为。捡起巨石并从物体衬衫的袖子上伸出来,第三个是用逼真的玩具枪的“射击”。知道不一个人在实验中受到伤害,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疼痛迹象,尤其是当他们自己做这些行为而不是看别人的行为时。实验表明,这是暴力本身,而不是道德的后果,这引起了厌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动不受有害后果的影响,而是意味着仅仅关注道德同情并不能说明整个故事。库什曼和同事得出结论:“对危害行为的自发反应反应可能会解释其他令人困惑的人类行为。在战场和虚假的道德判断中,人们拒绝直接伤害,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可以挽救许多生命。研究很多。对行为的反应是分开的SE观察意味着普通人具有一种心理机制,可以自动调整侵略性行为,从而自发地操作并间接控制意识。这种机制可以是自然的,是由基因提到的,也可以是获得的,也可能是我们可以快速学习的东西。存在心理机制,它具有抑制人际暴力的作用。